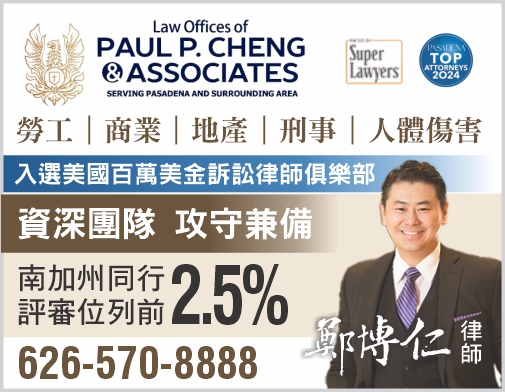【政治】「当美利坚帝国走向终结,很难不伴随着苦痛」《时代》杂志百大人物,弗格森看美国撤军阿富汗
时间:08/27/2021 01:00
浏览: 11941
当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撤军阿富汗,引发贾尼政府垮台、神学士武装席卷全国等骨牌效应后,西方国家争先恐后将本国公民与曾帮助过他们的阿富汗人撤出,国际媒体也对美国霸权的兴衰多所讨论。《时代》杂志百大人物、以经济史与帝国主义研究见长的尼尔‧弗格森(Niall Ferguson)指出,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,走的几乎就是百年前大英帝国(British Empire)衰退的老路,他也警告美国的衰弱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冲突与乱局。
在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、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弗格森,在2005年出版的《巨人:美利坚帝国如何崛起,未来能否避免衰落?》(Colossus: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)中,深入探讨身为超级强权的美国是否可能衰落,对外干涉的战争又会因何成败。在阿富汗政府垮台后,弗格森更在《经济学人》撰文警告,美利坚帝国的终结恐怕很难全身而退。
「民众依然蒙昧无知,那些只挂念选票的领导人,不敢让他们搞清楚发生什麽事。」邱吉尔,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第一卷
弗格森在文章开头就引述带领英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、并以《二战回忆录》抱走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邱吉尔(Winston Churchill)名言。这段话是邱吉尔对一战胜利者的描述,他们拒绝面对让人不快的事实,渴望继续受人拥戴、并且在选战中胜出,将国家利益置於度外。弗格森说,如今美国人民目睹了美军不光彩地从阿富汗撤走,总统拜登则奋力为自己决策所制造的混乱辩解。他们或许会发现,邱吉尔上面批评英国领导人的那番言词,听来竟有些刺耳。
以探讨大国兴衰着称的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・甘乃迪(Paul Kennedy)曾说,英国的精神状态是「国家精疲力竭」与「帝国过度扩张」的综合产物。1914年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、金融危机西班牙大流感,让债台高筑的「日不落国」面有土色。尽管英国仍是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,但早已不是无人能够挑战的强权。国内的贫富差距让左翼分子趁机要求财富再分配,一部分知识分子甚至走得更远,决定拥抱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。
20世纪初的英国除了国内局势动荡,对於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更是力所难及。昔日的全球主导地位,在欧洲、亚洲和中东都受到严重威胁。以国际联盟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系开始崩溃,只能靠着结盟来弥补帝国弱点的手段,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失败—既不敢承认极权主义的威胁,也没有阻止独裁者肆虐的手段。弗格森问道,这段英国的衰落史是否有助於理解今日美国?他认为美国与英国这两任全球霸权的比较,确实能发人深省。
弗格森说,美国当然不像上个世纪初的英国保有大量殖民地与附属国,美国国民多半也不认为他们是个「帝国」(不过美军确实在阿富汗驻紮了20年之久);美国的新冠疫情再严重,死亡率也不会像参加二战的英国那样凄惨(15至49岁的男性死亡率约为6%);美国更没有纳粹德国那样恐怖的敌人,带给他们明确而现实的威胁。尽管如此,「21世纪初的美国」与「20世纪初的英国」,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,两国在阿富汗建立秩序的企图最后都以失败收场。
专精经济史的弗格森,先从两个帝国的债台高筑谈起。
英国一战后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比例快速膨胀,从1918年的109%飙升到1934年的将近200%。美国的联邦债务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当年的英国不同,但是在债务规模上却是旗鼓相当。光是今年就会达到GDP的110%,甚至比他们在二战后的峰值还要高。国会预算办公室预估,这个数字到2051年将会超过200%。所以美国跟上个世纪的英国一样辛苦吗?弗格森认为,现在的美国可能更辛苦。
因为美国联邦债务的平均期限很短(约65个月) ,英国超过4成的公共债务是以永久债券或年金的形式发行,因此美国债务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比上个世纪的英国还要高得多。此外,英国在1925年决定将英镑恢复到战前的金本位制,这使得英国陷入了长达8年的通货紧缩。但英国的萧条相当温和,放松货币政策、货币利率下降,也意味着债务偿还负担的减轻,从而创造了新的财政操作空间。
但一般预料美国的实际利率将从2027年起转正,本世纪中叶更将稳步上升至2.5%。使一变化代表美国必须对债务支付更多利息,从而挤压其他联邦预算,其中当然包括国防支出—弗格森认为这正是症结所在。因为当年邱吉尔曾不断警告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跟日本的法西斯政权将会带来灾难,英国应该及早重整军备、应对乱局。但绥靖主义者却宣称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需要高昂成本,在财政与经济方面的限制下,当然无法快速重整军备。
弗格森说,今日美国面临的威胁当然与上个世纪的英国完全不同,但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与北韩确实都是强敌,而且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广泛的军事承诺,就如同上个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人一样,完全不去正视自己国家可能会跟独裁政权发生大战的可能性。弗格森认为,这就是美国的国防预算被认为将从2020年的3.4%下降到2031年的2.5%。当代的邱吉尔们大概都会对这个变化感到惊骇不已,而且这些人大概也都会跟当年的邱吉尔一样被指责是「战争贩子」。
当帝国实力不再
另一个英美帝国相似之处,在於帝国实力日益不复当年。根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‧麦迪森(Angus Maddison)的估计,英国经济到了20世纪30年代,除了早就被美国(早到1872年)超过,还被德国(1898年)与苏联(1935年)超车。弗格森认为,今天的美国也有类似的遭遇。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,中国的GDP在2014年就已迎头赶上。若以美元计算,中国目前的GDP是美国的75%左右,5年后则会达到89%。从人工智慧到量子计算,中国更被认为掌握了领先科技,这些都不是什麽秘密。
尤其中国今天作为美国的竞争对手,远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为强大。因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在冷战时期从未超过美国的44%。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崛起,领导人习近平的野心更是众所周知,一再表现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个人自由、法治和民主的敌意。过去五年,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明显恶化,但弗格森也指出,这似乎并没有转化为积极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共识。如果北京入侵台湾,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附和当年张伯伦(Neville Chamberlain)首相的看法。他当年曾将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描述为「发生在遥远国度,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民族之间的争吵」。
弗格森表示,当年英国会在两次大战之间表现软弱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知识分子对帝国观念的反抗,或者说对传统英国价值观的反抗。邱吉尔曾回想1933年牛津大学辩论队的辩题—我方拒绝为国王和国家而战—并且语带厌恶地表示:「在英国,人们总是对此一笑置之。然而在德国、苏联、义大利、乃至於日本,对於英国已颓废堕落的看法却是根深蒂固。」弗格森认为,这也是如今中国那些战狼外交官与民族主义分子对美国的看法。
当帝国走向终结
如同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对於帝国的观念嗤之以鼻,现在美国的左派跟右派也习惯性地嘲笑或辱骂帝国。《国家》杂志(The Nation)的记者汤姆‧恩格尔哈特(Tom Engelhardt)幸灾乐祸地说: 「美利坚帝国正在分崩离析」,在政治光谱更右边的经济学家泰勒‧考恩(Tyler Cowen)忙着想像「美利坚帝国的衰落会是什麽样子」,更左边的非裔哲学家柯内尔‧韦斯特(Cornel West)则说「黑命贵,对抗美利坚帝国的战斗也是」。两位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甚至说,这场新冠疫情就是美利坚帝国「没穿衣服的德性」。
弗格森不无感慨的说,美国的右翼仍在扞卫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叙事,左翼人士则试图将美国历史重塑为奴隶制与种族隔离的故事。但位於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,就是没多少人会去怀念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全球霸权时代。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一样,21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已经不再热爱帝国主义—这个事实已经受到中国的关注—然而帝国依然存在。
诚然,美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殖民地。即便算进波多黎各、加勒比海的美属维尔京群岛、北太平洋的关岛、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、南太平洋的美属萨摩亚,按照当年英国的标准,这份清单实在微不足道。但弗格森锐利地指出,美军的军事基地却像当年英国的殖民地一样遍布全球,美军部署在150多个国家,常驻海外的部队人数超过20万。维持这支大军当然不容易,但认为摆脱它会更容易,更是一种错觉。
弗格森认为,拜登思虑未周地决定从阿富汗撤军,是美国总统想要减少海外承诺的最新讯号。最早从欧巴马仓促地撤出伊拉克开始,他甚至在2013年宣布「美国不是世界警察」;川普的「美国优先」则是出於相同冲动的民粹主义版本。何况撤出阿富汗就是川普的点子,他渴望用关税代替反叛乱行动。问题是想从全球主导地位上抽手,通常难以全身而退。
弗格森说,不管如何解释,宣布放弃这场漫长战争就意味着失败,不仅神学士这麽看,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、更北边的俄罗斯,也都看在眼里。当年欧巴马宣布放弃全球责任之后仅仅几个月,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和叙利亚进行了军事干预,弗格森认为这绝非巧合。如果回头看更早的越战,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屈辱,确实鼓励了苏联及其盟友制造更多麻烦:包括非洲南部和东部、中美洲以及1979年入侵的阿富汗。
弗格森指出,美利坚帝国的终结其实不难预见,即使是在2003年成功入侵伊拉克,新保守主义的狂妄自大达到高峰之际,也能够看出些许端倪。正如他在《巨人》一书中所提到的,当时美国的全球地位已有四个根本弱点浮现,包括人力短缺(没什麽人愿意长时间待在阿富汗或伊拉克)、财政赤字、注意力不足(选民很快就对大规模干预失去兴趣)以及历史短视(政策制定者不愿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)。
比起百年前的英国,今天的美国更糟糕的是其净国际投资部位(NIIP)是负的,而且略低於GDP的-70%。这意味着外国对美国资产的所有权,已经超过了美国对外国资产的所有权。相比之下,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NIIP仍是正值。抛售帝国白银(确切地说,其实是迫使英国投资者出售海外资产并交出美元)是英国为二战买单的方式,但美利坚这个伟大的债务帝国,却没有相应的储备金。只有向外国出售更多国债,它才能负担得起维持世界霸权的成本—这显然会是让一个超级大国岌岌可危的不稳定因素。
弗格森认为,邱吉尔在《二战回忆录》里并不是想说德国、义大利与日本的崛起势不可挡,因此造成了英国的衰落。这位英国名相想说的其实是,如果民主国家能在20世纪30年代更早采取更果断的行动,战争是可以避免的。当年美国总统小罗斯福(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)曾问邱吉尔「这场战争该叫什麽名字」,邱吉尔立刻给出答案:不必要的战争(The Unnecessary War)。
跟当年的德国、义大利、日本一样,弗格森认为中国(以及俄罗斯)的崛起当然也并非势不可挡,那些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国家—不管是委内瑞拉或是北韩—更都是些自身难保的政权。中国人口快速老化、劳动力正在减少,私营部门的庞大债务正在拖累经济成长,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置失当,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,工业部门对燃煤发电的高度依赖,更有可能让中国成为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。
虽然中国自身的问题不少,但在弗格森看来,眼下一系列事件的发展,却很有机会导致21世纪版本的「不必要战争」—其中可能性最高的就是台海战争。习近平觊觎台湾已久,美国则是含糊其词地承诺要保卫台湾。不过随着东亚军事平衡的严重倾斜,美国的承诺日益显德可疑。包括中国反舰飞弹对美军航空母舰的威胁性越来越大,就是五角大厦始终没有解决良策的难题之一。
弗格森说,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威慑失败了,而中国真的选择挺而走险——美国将面临两个严峻的选择:像英国在1914年(一战)或是1939年(二战)那样,打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争;还是像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那样折戟沉沙。邱吉尔曾说,他写《二战回忆录》是为了说明「恶意是如何被善良人的软弱所强化」、「基於对安全与和平的渴望所采取的中间路线,如何导向灾难的靶心」,单纯的善意并不见得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。
弗格森在这篇写给《经济学人》的长文结尾说:美国的领导人这些年过於热衷於梦想,从小布希领导的新保守派想要「全方位主导」,到川普在就职演说中以「美国浩劫」( American carnage)来形容这个国家的黑暗与凋敝。当另一场全球风暴到来,弗格森除了用邱吉尔在《二战回忆录》第一卷的结语—「事实胜於梦想」(Facts are better than dreams)作为警世之语,他也呼吁美国「也许是时候面对邱吉尔深有体会的事实了:当帝国终结,很难不伴随着苦痛」。
风传媒

图片翻摄自网路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
 点评
点评 微信
微信 微博
微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