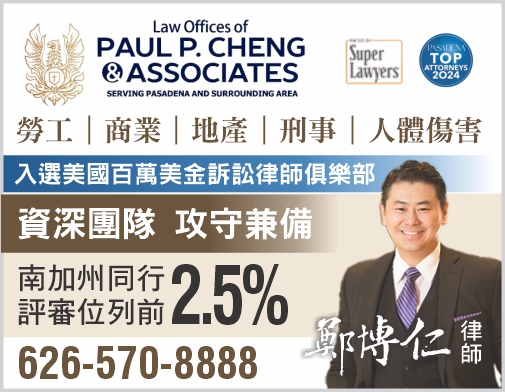马来西亚锁国以后:星马边境防疫下的「移动公民」
时间:03/19/2020 00:00
浏览: 3873

3月15日,新加坡宣布境外隔离措施扩大至全东南亚,但从马来西亚透过陆路或水路入境者,则不在此限。新加坡隔离措施正式上路隔天,马来西亚即宣布更严格的「行动管理限制」措施,即自3月18日起至31日实施出入境管制,取消集会活动,及停止大部分不必要的商业行为。
这表示,在马来西亚的「锁国」政策下,新加坡不限马来西亚人入境的但书宣告失效,因马来西亚人已被马国政府限制出境。新加坡的这项但书自有其考量——有将近40万马来西亚人,每日往返新加坡工作与求学。此外,也考量新加坡国土面积对人力与物资的需求,周遭国家的异动都会造成影响,因此在马国宣布封锁的隔日,新加坡政府紧急说明粮食储备无虞,两国物流不受影响,以稳定民心。
马来西亚的临时性锁国政策并非突如其来。自从多起确诊案例均被追溯至一场2月28日的伊斯兰万人宗教活动,已可预期群聚感染终成定局。在发布封锁命令前,马来西亚陆续新增300例左右曾参与此宗教活动的确诊案例。相邻的新加坡、印尼与汶莱,也纷纷出现参与者返国后确诊之案例。
由於参与者名单难以追溯,马国政府只能一再呼吁人们主动前往检验。而封锁14天的用意,是基於病毒潜伏期特性,并争取找出确诊者的缓冲时间。

有将近40万马来西亚人,每日透过新柔长堤往返新加坡工作与求学。左图摄於3月17日,右图为管制生效后的18日
新加坡的防疫政策
2月初,新加坡一度是中国以外确诊数最高的国家。第一波确诊数急升是2月初的群聚感染,包括教堂与企业会议群聚;第二波是在3月初,发生在战备军人俱乐部感染。
第一波感染后,总理李显龙发表健康者无需戴口罩、轻症者在家修养维护医疗资源的谈话,被放在与台湾的严防政策相较下,一度被解读为自我放弃的「佛系防疫」。佛系防疫,这个带有贬义的形容,如今也被用在日本和英国。仅仅在一个月后,新加坡确诊案例趋於稳定,又被解读为另一种防疫模范:政府高效调度、医疗分配以及人民信任。
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」(PHPC)是其中重要的医疗政策之一。因应新冠肺炎,新加坡全国大约900家全科诊所(GP Clinic)启动为「公共卫生防范诊所」。在此合作框架下,医疗人员平日即接受政府训练以应对紧急状况,过去也曾因雾霾问题(空污)与H1N1启动过。
出现呼吸道症状者被要求先前往此诊所做初步检验;一旦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,就能以最小单位全面关闭与消毒,减少传染之余,也能迅速恢复运作,达到患者分流目的。高医疗覆盖率与国家面积小优势,都有助於短时间内追踪病毒来源。
学校未曾停课、大型聚会维持但限定在250人以下,以及鼓励职场和外出时的安全社交距离。只要体系未崩溃,早已形塑的官僚防疫体系仍可持续运作。而要让体系不崩溃,除了预防与降低感染人数,也需要保持经济运作,才足以维持昂贵的防疫开销。随着战备军人俱乐部晚宴的群聚感染发生(至今有38起关联确诊),新加坡的防疫模式最终会被如何解读,还会持续变化。当透过新闻理解他国疫情,可能更多是以结果论来回溯理解。
对新加坡而言,除了必须考量自身脉络,国际与区域互动与变化也会深受影响。而基於地理因素,新加坡每日有大量来自相邻的��来西亚柔佛州与印尼巴淡岛人口往来工作,虽然有国界之分,但交流极为频繁。
星马两国的防疫合作
星马两国在防疫初期就已展开情报合作。新加坡第一例确诊者为武汉游客,家属在其确诊后继续旅游至马来西亚,接获新加坡通报的马国政府将游客带往检验后,成为该国的首三例确诊者。2月初,两国高调宣布成立联合防疫,不过在复杂因素下,仍旧无法避免两国疫情后续发展。
在东南亚各国中,星马两国是新冠肺炎蔓延初期,最早积极限制外国人入境的国家。新加坡除了自2月1日禁止中国大陆入境,往后分别在2月26日针对韩国大邱;3月4日伊朗、韩国全国与义大利北部;3月16日瑞士、英国、日本与全东南亚国家;3月18日法国、义大利全国、德国与西班牙都相继禁止入境。
一海之隔的马来西亚,禁止令则是1月27日武汉与湖北(之后增加浙江与江苏);3月5日伊朗、义大利、南韩与日本各别城市、3月13日提升至全国;3月14日丹麦;18日则落实14天全境封锁。虽然时序上稍有落差,基本与各国确诊病例数增长成正相关。
不过,除了最初扩散的中国,后来禁止入境的国家清单多为防疫作用,而不是基於已有案例实际扩散至本土。又如义大利与韩国,最初仍是以城市(北义大利与大邱)为单位禁止。新加坡作为航空枢纽,平日接受繁忙国际转机航线,疫时仍尽可能地维持运作。
直至3月以前,星马两国都有一段高出院比的时期。2月27日,马来西亚总数24例确诊者中,就有22人重复测得阴性而康复出院;新加坡则是96名确诊者,其中66人出院。眼看疫情得到最佳控制,但新一轮感染扩散,患者的康复速度至今无法赶上病毒感染的增长,星马两国也在各自防疫脉络下实行进一步封锁,却也同时息息相关。
星马人口的流动关系
新加坡的570万人口中,外来人口约168万,相等於30%。近年外来人口持续增长,新闻里不时出现零星的文化冲突,导致新加坡人对外来者的增长更为警惕。2016年,政府制定减少外来人口政策,曾创下连续两年负成长,并在政策上持续降低特定领域的外来名额。不过,历年永久居留权的取得人数则变动不大。
由於星马两国历史与文化相似,马国人自然成了与星国文化最相近的「外来者」。在现有组成人口中,有将近100万人是马来西亚移民。马来西亚实施禁止出境命令后,首当其冲的,正是每日往返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。
除了政治与文化,经济无疑是促成往来频密的因素之一。随着近十年来马币疲弱而新币步步升高,不少马来西亚人倾向到新加坡工作,同时居住位於马国边境的柔佛州。每日往返通勤,得以藉由两国消费水平差异,一方面领取新加坡薪水,另一方面在马来西亚消费,间接提高收入效益。与此同时,新加坡也不必承受居住负担。
理论上此生活形态是一种可持续的长远方案。新加坡一般会让长期工作者取得永久居留身份,虽必须履行缴纳相应税率义务,但也能享有大部分等同国籍的权利,例如防疫期间制定的每户四片口罩政策,国民与永久居留皆列为优先对象。唯独不可碰触的是政治权利,在「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政治」的方针下,永久居留者无法投票,且依然被视为「外部干涉」。
瘟疫蔓延时的「移动公民」
人们一方面可以理解疫情时期维持工作的重要,另一方面又对於因为钱(工作换来的「薪水」,此时常被简化成「为了钱」)而外出者较低容忍。这其实是日常与例外出现交错的结果。
过往我们习於全球化时代提供的人口迁徙便利,让以旅游、学生与工作为目的的出入境变得便捷,免签数量更常被视为国家外交成功与否的指标之一。一份标准的长期外派职缺,会说明一年可获得的返国机票次数或相应假期。除非是特殊目的国,一般不会将出入境困难视为考量因素。「出国」这个举止由「移动/流动」代替,异地的工作岗位往往只是在权衡下所做的一个职场选择,无关忠诚或共同体。
在防疫时代,「国家/边界」重新占据明显可见的位置。当地住民往往会要求政府实施更严格的边界控制,无论对象是已确定或只是潜在可能的疫区。边境管制更可作为一种明显「有感」的控制力,来防止疫情入侵。国籍所意味的共同体,在此时展现了它之於现代国家的意义,虽然很少人真的会自行选择国籍,但国籍仍与自身权利相连,比如透过本国国籍的身份,可在封锁边境时被允许入境(除非所在地已禁止出境)。
移动公民在防疫时代,还能移动吗?移动后,还是公民吗?以马来西亚边界封锁为例,若任职的国外机构为必要产业,依然可以出境,但必须在边境封锁结束后方可入境。减少外部输入病毒在防疫上似乎有其必要。新加坡更曾以检疫者擅自离境而剥夺其永久居留权,但永久居留与国籍毕竟有异。主观来看,人被分为国民与非国民,但在瘟疫蔓延时期,境内与境外的区分似乎变得更为重要。境内自然地形成共同体,人们更意识到对境内移工(包括无证件移工)和弱势者保护的重要,而对境外入境者抱有警惕。
新加坡在最近一次提升入境令时,曾表示意识到有人特意入境寻求治疗,会对医疗造成负担。除了扩大禁止令,也要求持旅游或短期签证者在确诊后,需全额负担医疗费用。境内者成了优先守护的对象,而随着确诊数增加,即便是少数的境外移入案例也会显得刺眼。这点不仅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,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。
小结
为应对马来西亚的禁行令限制,新加坡政府赶在正式实施前,呼吁国内雇主协助提供马来西亚籍员工临时居住地,以度过限制期。人力资源部宣布已为超过1万名马来西亚人找到住宿。
新加坡两大运输机构SBS与SMRT(包含地铁、轻轨、公车与计程车业务)紧急安排马来西亚籍雇员暂住饭店,也在脸书强调感谢愿意留在新加坡服务,并唤起合作共同体。目前,网路舆论均呈现正面态度,比如网路媒体SGAG,略带煽情地以「选择出走新加坡,以确保他们所爱的人回家后不会挨饿」来描述这群连夜过境者,也赢得多数赞赏。
马来西亚封锁边境的本意是避免病毒移入与输出,但一时间大量因工作而在封锁前连夜过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,却给予边境防疫莫大压力,反倒可能造成防疫缺口。积极维持日常经济运作、且近期本土案例已趋於和缓的新加坡,是否能避免病毒因此移入,都需视政府接下来的反应而定。若是最终造成扩散,又要如何维持上述的温情评价?
马来西亚的禁出国命令虽暂定3月31日结束,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排除延长的可能性。新加坡无从决定时间,而是取决於马来西亚内部能否在封锁下达到防疫效果。只是一旦政策被看不到终点似地延长,届时除了物资上的负担,也会对心理造成巨大的压力。
文章摘自:联合新闻网
图片翻摄自网路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,我们将及时处理。
 点评
点评 微信
微信 微博
微博